二、核心图案为五指律符在音乐神话传说的包围下,曾侯乙筑上的这组图案必定也与音乐有关,只不过包裹着一层奇特而神秘“外衣”,需要认真加以辨析(图6)。从色彩上看,这组图案黑红相间,特别单调,与周围灵动的图案并不十分协调。从尺寸上看,这组图案占用的面积分别小于“夏后启得乐图”和“伶伦作律图”。图6从线条上看,这组图案采用的是抽象的笔法,比一般的绘画要简单一些,尤其不如两幅神话传说使用的形象化的笔法。有人认为,这组两行连续方块形图案,是起装饰作用的变形云纹或勾连卷云纹,但仔细观察好像与云纹不大沾边,况且云纹作为辅助图案应当安排在画面的边缘或穿插在主题纹饰的中间,不应当像筑上的图案那样单独占据着最突出、最显眼、最核心的位置。有人认为,这组两行连续方块形图案,是仿青铜器上的一种云雷纹。云雷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典型的纹饰,其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所构成。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云雷纹常作为青铜器上纹饰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而筑上的方块形图案并没有“回”字形线条,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主题纹饰。那么,曾侯乙筑上的这组核心图案究竟记录着怎样的信息,又向人们表达着什么事物呢?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连续方块形的图案中,靠近内侧的一边紧紧相连,而靠近外侧的一边却留有缺口,将连续图案有机地分割开来。从分开处判断,每行有12个方块,两行共有24个方块,这与筑的正面和侧面的凤鸟纹数量及其排列方式基本相同。其次,尽管每个图形勾画都有差异,但却似乎都像人手的五个指头,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伸开,有的卷曲。笔者选择出三个比较典型的图案,分辨出人手的五个指头:姆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图7)。如果每个图案代表着一种操琴指法的话,那么曾侯乙筑上描绘出来的就是12种操琴指法。图7再次,联系周边对应的是五组均为12只凤凰的环境分析判断,可以认定这是古人使用筑一类琴瑟弹奏十二律的指法,通过这些指法,能够在琴瑟上弹奏出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ruí)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如此,十二种指法可以命名为“五指律符”。这是使用弦乐器演奏乐曲的基础,是记录乐谱的元素,是校正琴瑟的基准。这就完全解释清楚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唯独这组包围在音乐神话中的符号,恰好处于筑的中心位置,成为整个图案的核心和灵魂。有人提出疑问,弦乐器演奏时的差别很大,有的是弹弦,有的是拉弦,有的是拨弦,还有的是击弦,都可以用五指来表示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使用弦乐器时总有一只手是在抚弦或按弦或拢弦或揉弦,必须并用五指,因此都可以用五指律符来表示。这里牵扯到一个在音乐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包括筑在内的琴瑟演奏得以传承下来,是否有乐谱呢?如果有的话,这种乐谱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记录下来的呢?这一问题在古籍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记载。如果按照乐谱是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或文字的定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引用的一个故事或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卫灵公去晋国,在濮水边休息时,深更半夜听到鼓琴声,于是他问左右人员,都回答没有听到。卫灵公立即召来音乐家师涓说:“我听到了鼓琴的声音,周围的人都没听到。这种声音好似鬼神。你为我听而写之。”师涓答应后,“端坐援琴,听而写之”。第二天,师涓对卫灵公说:“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卫灵公答应后,师涓用了一整夜时间练习好,并报告了卫灵公。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三点:第一,春秋战国时是有记录乐曲的乐谱的。不过,需要有专业人员才能记录下来。第二,乐谱记录的并不是音乐的旋律,即每个音的音高和拍节,而是相应的抚琴的指法,所以要“端坐援琴”才能“听而写之”。第三,这样记录下来的乐谱并不能马上演奏出来,还需要经过彻夜整理,把抚琴的指法“还原”为音乐的旋律,按照现代的语言,就是“打谱”,完成后才能演奏。曾侯乙筑上所使用的正是这样的记谱方式,即以符号标明指法,以指法表明音律。这种原始的、古老的方法,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一直传承并发展到清代。三、五指律符所表现的古代音律这里需要用通俗的语言,普及一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中国古代音律知识。律,本来是指用以定音的竹管。蔡邕(yōng,音庸)《月令章句》:“截竹为管谓之律。”古人用12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12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因此这12个标准音也叫做十二律。用现代音乐语言来说,就是将一个八度音程划分为12个单位,在律学中称为“律”,在音乐实践中称为“音”。那么,古人按照什么方法来划分十二律呢?就是《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即以黄钟为准,将黄钟管长三分减一,得六寸,就是林钟的管长;林钟管长三分增一,得八寸,就是太簇的管长;太簇管长三分减一,得五又三分之一寸,就是南吕的管长;南吕管长三分增一,得七又九分之一寸,就是姑洗的管长;以下的次序是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除由应钟到蕤宾,由蕤宾到大吕都是三分增一外,其余都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增一。这就是十二律相生的“三分损益法”。这一方法至少诞生于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在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构建了古代中国完全独立的音乐体系,而且奠定了我们民族音乐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直到明代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朱载堉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创制了“新法密律”,才使古代的十二律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在“新法密律”的启发下,18世纪西方最终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成为现今通行的世界音乐体系。古代十二律由低到高的音阶排列顺序如前所述,其中又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阳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是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那么,曾侯乙筑上的五指律符是如何排列的呢?笔者在资料尚不完整的情况下,经过初步辨认,推断是按照十二律由低到高的音阶顺序排列的,即从右到左排列,上部以阳律的黄钟打头,下部以阴律的大吕打头(图8)。图8按照一般的规律,用图案或符号记录乐律,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定型的过程,伴随着这个漫长的过程,表示乐律的图案或符号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形、不断简化,逐渐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图案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符号会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完全脱离了最初的形象。五指律符也是这样,开始是忠实地、形象地记录琴瑟演奏的音律指法,之后成为一种固定的图案或符号,再经过各种音乐实践的洗礼和检验后,不断地删繁就简,不断地改进变化,最终由相对复杂的图案变成了相对简洁的符号,逐渐脱离了最初对于描绘五指的多余笔画,完成向五指律符的“蝶变”,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乐谱。四、古代音律的五指律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指出,曾侯乙筑上的这种五指律符,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在墓中相当多的琴瑟上,五指律符都反复地出现过。最典型的就是在曾侯乙墓考古报告中披露的一件25弦瑟。曾侯乙墓共出土12件瑟,7件出自中室,5件出自东室,共有三种类型,均为25弦。相传伏羲作50弦瑟,致使音调过于悲伤。于是到了黄帝时把瑟断去一半,改为25弦。琴与瑟常并称,比喻和谐美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有18、19、21、23、24、25弦共六种弦制。图9曾侯乙墓考古报告披露的这件25弦瑟,通长167.3厘米,宽38.5–42.2厘米,侧高11.1厘米,通体髹漆(图9)。在瑟两边的侧板上,均绘有两组由10只凤鸟组成的图案。凤鸟的姿势、神态、衔接,几乎与曾侯乙筑上的一模一样(图10)。只不过粗看比曾侯乙筑上少了2只,但细看发现,其上的凤鸟有2只仅露出了个小尾巴,大部分鸟身没有描绘出来。图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组凤鸟图案的旁边,对应的还有两组五指律符! 每组律符的方块都是12个,表示着十二律(图11)。这就明确无误地证明,五指律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成熟,是上层社会和音乐家们记录音律的工具和法宝。图11最让人称奇的是,在曾侯乙墓东室出土了四件彩漆木雕盖豆,形制接近,均为整木制成,盖与耳上有浮雕纹饰,两侧附加方形大耳。盖顶上浮雕三条龙,互相盘绕。方耳浮雕成类似编钟鼓部等处纹样的龙纹装饰。特别是器身上环绕着的纹饰,竟然也是五指律符。如果细数,一件周围是24个律符,一件周围是12个律符。它们与曾侯乙筑一样,纹饰中均绘有黑红相间的菱形边框(图12)。图12豆,是古代的一种礼器,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作为礼器的豆,与鼎、簋(guǐ)、簠(fǔ)、笾(biān)、铏(xíng)、罍(lěi)、爵等配套使用,非常神圣。这四件豆出现在曾侯乙墓的东室,上面又描绘着五指律符,说明使用它们与音乐有关,很可能是盛放已经朽烂无存的琴弦或者已经散落的瑟柱。据考古报告称,从曾侯乙墓淤泥中清理出来的瑟柱达98件,推测当初它们是放置在豆中的,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后散落入泥中。古往今来,把转瞬即逝的优美音乐用一系列抽象的图案或符号记录下来,形成乐谱,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用文字、图案或符号以及表格记录音乐这美妙的声音,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数艰辛的探索,尝试过多种方式,设计出不同方案,创造出许多奇异的乐谱。而曾侯乙墓中展示出来的编钟乐谱和五指律符,就是最初的发明创造,它们为后来中国人发明的工尺谱、琴谱、半字谱、弦索谱、管瑟谱、俗字谱、律吕谱、方格谱、雅乐谱、曲线谱、央移谱、查巴谱、锣鼓谱等乐谱,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曾侯乙的编钟乐谱和五指律符,与古代的方块字、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一样,展示了足以让中国人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世界文明之光。2020年12月1日于北京本文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谭维四)》《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曾侯乙文物艺术》《曾侯乙编钟(邹衡、谭维四)》《曾侯乙(湖北省博物馆)》《中国音乐史(司冰琳)》来源: 光明网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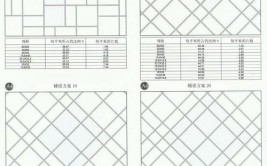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