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的犹太省长“所罗巴伯”。很快,中世纪的读者开始为自己拥有的书卷制作索引。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进一步的改进。此前在个别手稿中已经出现页码编号,但印刷书籍的统一性赋予了页码另一种用途,即在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中标注同一位置。这种想法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流行起来。第一个印刷页码直到1470 年才问世;即使到了 1500 年,也只有少数书籍采用了这种做法。相反,早期印刷的索引所指向的是文本位置或页面底部的标记(“Aa”“b2”等),印刷厂和装订者用这些标记来保持成品页面的正确顺序。但到十六世纪,页码的使用得到了推广,同时学术著作的索引也越来越复杂。早在 1532 年,伊拉斯谟就以索引的形式出版了整本书,因为他打趣说,如今“很多人只读索引”。几年后,他的同事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当时最伟大的索引编撰者之一——大肆赞美这种新的搜索工具如何改变了学术研究:它为学者们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仅次于活字印刷术这一真正神圣的发明……在我看来,人生短暂,无论对于从事何种研究的人来说,书籍索引都是绝对必要的。与阅读和学习习惯从古至今被广泛认知的每一次变革(文字的发明、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推出、ChatGPT的诞生)一样,索引的传播也与人们的焦虑相伴,担心浮躁、肤浅的信息获取方式正在取代“正确的”阅读和理解习惯。十六世纪的伽利略就曾抱怨说,科学家在寻求“自然效应的知识时,并未亲身去接触船舶、弓弩或大炮,而是退到书房里,翻阅索引或目录”。乔纳森·斯威夫特在 1704 年调侃道,“通过浏览索引来假装理解一本书,就好像一个只看到了花园角落里的厕所的旅行者要去描述一座宫殿那样”。然而,正如邓肯明智地指出的那样,我们获取知识的习惯一直在变化,而且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和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而且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千差万别。推特、小说、短信、报纸:每一种都需要不同的关注。年龄越大,我们对自己熟悉的阅读方式就更加投入,而对那些似乎有可能颠覆这些阅读方式的技术就更加疑心重重。十八世纪出现了大量新奇的索引形式,包括搞笑之作和实验创作,《索引的历史》对此类编目颇有兴趣。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索引似乎可能成为几近所有写作体裁的一部分,包括史诗、戏剧和小说;包含索引已成为一种文学地位的象征,是作品声名显赫或书籍制作豪华的标志。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篇幅浩繁、畅销不衰的《伊利亚特》为他赚取了一大笔财富,其中包括几张宏大、详尽、复杂的表格和索引(其中一张列出了荷马作品中从“焦虑”到“温柔”的各种情绪)。1750 年代,塞缪尔·理查森为他的小说巨著《克拉丽莎》编制了长达八十五页的索引(还包括索引本身的索引)。这其实并不是正文的参考资料,而更像是对这本分为七卷、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中所包含的道德训诫的总结。他将其称为“情感列表”或(全称)“《克拉丽莎》创作历程中所包含的道德和教诲性情感、告诫、警句、思考和观察的合集,据推测具有广泛效用,并在适当的标题下进行了摘录”,甚至想过是否要将其作为一部作品单独出版。印刷起家的理查森虽然对编制“抽象”索引情有独钟(他后来还为自己的三部小说编制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统一索引),事实证明这终究是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夭折的分支。毕竟,与思想和情感相比,名字和事实更容易检索。与这个夭折的分支相对照的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虚构文学作品与非虚构作品的体裁日益分化。非虚构作品的索引编撰也更加活跃,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雅克·保罗·米涅(Jacques Paul Migne)在1850年代编撰不朽的《教父著作全集》(二百一十七卷)的同时,同样庞大的四卷本索引也一同问世。五十余人用了十年时间来编撰这套高达二百三十一个分部的索引,按作者、主题、书名、日期、国家、等级(教皇排在红衣主教之前、红衣主教排在大主教之前,如此等等)、体裁以及其他数百个分类——包括天堂和地狱的单独索引。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工作者联合起来,编撰了一部包含所有现存最重要书籍和知识的国际通用索引——与此同时,还有第一部规模较小但仍非同寻常的全球期刊出版物索引。另一方面,在现代小说中,索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种文学构想出现:对体裁、虚构性和事实性的玩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J. G. 巴拉德都曾以索引形式创作过小说(在这两部小说中,Z结尾的最后一个条目揭示了情节的最终转折)。在索引这一多样化领域中,邓肯堪称是一位全面而极具启发性的领路人,但他笔下的人物仍以男性居多。他指出了自1890年代以来,随着秘书事务所的出现,索引编撰者逐渐由女性主导,如今这个领域的绝大多数从业者都是女性——包括他自己这本书中精美索引的编者宝拉·克拉克·贝恩。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这一点进一步深究。那个时代无数书籍的序言都能够深入地引发人们对二十世纪学术索引编制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化、父权制、等级制劳动的反思。1983 年,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在完成编辑意义重大的十一卷《塞缪尔·佩皮斯日记》后,编撰了一份通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英文索引。十三年前这套丛书的第一卷问世时罗伯特遭遇了家庭不幸:就在书即将付梓之时,与罗伯特相伴三十年的妻子艾琳突然去世。满怀痛苦的编辑在鸣谢部分的末尾以上世纪中叶男性学者的标准措辞写道:“已故的罗伯特·莱瑟姆夫人阅读了许多校样,除此之外,她也给予了无法衡量的帮助。”等到他要为全书索引卷撰写鸣谢时,莱瑟姆已经再次幸福地开始了婚姻生活,性别运动甚至也已席卷剑桥。他此时的言论让人联想到一个更加轻松、不那么明显的沙文主义世界,同时也为家庭式编撰索引工作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我的妻子林内特也参与了本索引的编撰过程。我制定基本计划,但她参与了编制的每一个过程。她大声读出日记全文,我同时记下注解——我们一边读一边讨论,到底用什么词汇来引出各组参考资料最为合适,这样就把本来可能是件苦差事的工作变成了纸上游戏。她在后期阶段对细节进行了无数次核查,并从文本中核对了排印稿中的每处参考资料。作为莱瑟姆家的共同事业,他的妻子精力充沛,组织能力强,而且文笔风趣。他曾向索引编纂者协会详细介绍:实际上,这项工作常常让人捧腹大笑,成为一种游戏而非职务。事实上,索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字游戏,为一系列相关主题的综合标题或口头说法寻找合适的代表词汇;莱瑟姆夫人在文字游戏方面颇有专长,许多解决方案都归功于此。在这个时代,并非每次这样的基于婚姻的合作都如此和谐。1970年代中叶,美国标准产科教科书的新任主编杰克·普里查德(Jack Pritchard)请妻子西格妮帮他编索引。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她是一名护士、母亲、女权主义者,不久前她把自己的头衔改成了“Ms.”;他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种种男权态度显然激怒了她。在索引完稿后,读者可以发现她列入了“沙文主义,男性,数量不等,1-923页”(也就是书的每一页)。在四年后的更新版中,她把这个条目改为“沙文主义,男性,数量巨大,1-1102页”,她还附加了一句对此工作的整体评判:“很难说这是用爱发电,1-1102页。”也许她听说过《纳尔逊儿科教科书》。在第六版问世几个月后,安·纳尔逊考上了大学。她在1954年毕业后,与一位有抱负的律师理查德·E.贝尔曼(Richard E. Behrman)成婚。据他后来回忆,在同意结婚之前,“安让他保证,如果要写教科书,永远不会叫她来打下手”。但没过几年,在第七版教科书即将完稿时,她专横的父亲再次要求安(此时已经是“理查德·E.贝尔曼夫人”了)和姐姐弟弟一起帮他编索引。她屈服了——但报复性地夹带了私货。在“毫无价值”(Birds, for the)条目下,她列了整本书,从第1页到1413 页。永远不要和索引编者作对。(本文英文原文刊于2023年6月23日《纽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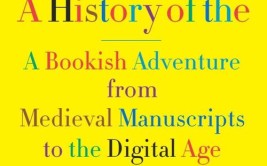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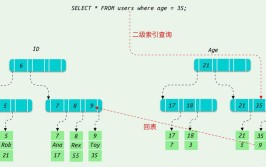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