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2017)鄂28刑终149号(2017)鄂2801刑初366号(2018)鄂28刑终42号(2020)鲁17刑终292号(2015)高新知刑初字第2号(2019)鄂1123刑初122号(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罪与非罪案件发回重审时(第二份判决),赵某、张某、陆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侵犯著作权罪)均有异议,贾某表示自己对罪名不了解,但是上诉后也和其他三人意见一致,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赵某认为:海豚软件是其独立开发的软件,和涉案游戏之间并不存在复制关系——“海豚软件没有任何一处与《战地之王》或《英雄联盟》是相同的”;自己没有传播他人作品,不构成复制发行行为,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本案应属民事纠纷,不应入罪。张某提出自己一没复制,二没发行,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罪行为特征,因此不构成犯罪,请求改判无罪。陆某则提出:其负责管理一般公众都被允许使用的QQ,管理期间没有其销售外挂的证据;与赵某的关系是雇佣关系,约定工资3000元,工作内容不涉及外挂销售,因此与赵某等不属于共同犯罪;自己参与过软件测试,但参与测试的软件尚未销售,没有产生经济利益。贾某上诉时提出:没有参与任何软件的制作、销售与传播,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客观行为,从犯罪构成上不能成立侵犯著作权罪,且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未参与任何钱款交易,未使用任何账号为赵某收钱,无任何获利行为;不知晓赵某制作的软件为外挂软件,只以为是一般的软件,帮助赵某管理QQ群实属帮忙,主观上缺乏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故意,请求改判无罪。法院评价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被告人的相关意见。关于赵某提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不成立。法院首先对“外挂程序”的营利性、未经许可性、对通信协议的破译与擅自使用、对游戏数据的截取与修改等特征进行说明。“网络游戏外挂程序是他人利用自己的电脑技术专门针对一个或多个网络游戏,通过改变网络游戏软件的部分程序制作而成的作弊程序,其复制了互联网游戏程序的源代码中的部分内容,研发网络游戏外挂程序须以网络游戏原有程序为基础,存在着复制网络游戏数据的客观事实”。“外挂程序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破译和擅自使用了网络游戏的通信协议,通信协议又称通信规程,是指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即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作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只有经过网络游戏经营者的许可,才可以使用网络游戏的通信协议”。“网络游戏外挂程序破译并擅自使用网络游戏的通信协议,截取并修改游戏发送到游戏服务器的数据,修改客户端内存中的数据,以达到增强客户端各种功能的目的”。然后基于上述特征,指出制作、销售网络游戏外挂程序行为具有侵犯著作权罪所规定的“复制发行”特征,可以认定为该罪。“外挂程序这种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游戏通信协议的行为,进一步说明了制作、销售网络游戏外挂程序行为的侵犯著作权特性”。“制作、销售网络游戏外挂程序的行为基本符合侵犯著作权罪所规定的“复制发行”的要求,可以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其中,“……改变网络游戏软件的部分程序……”,“……复制了互联网游戏程序的源代码中的部分内容”,“研发网络游戏外挂程序须以网络游戏原有程序为基础,存在着复制网络游戏数据的客观事实”源自“网络游戏外挂程序”的定义而非在案证据(判决书中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远程勘验工作记录、电子证物检验报告、鉴定意见没有相关描述,但可能是受篇幅所限)。判决没有注明定义出处,同类内容在前几天写过的2014龙泉驿CF外挂案中也出现过。不过两案判决中均没有与“外挂程序及游戏软件程序”比对相关的内容,而这是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与“复制”相关的,用于判断是否存在镜像复制、实质性相似、代码或程序结构与效果相似等情形的常见依据。龙泉驿案件中证据中是有一项“均出自同一源代码、具有同一性”的鉴定报告,但该鉴定是针对不同名称的外挂程序所做的比对,而非游戏程序与外挂程序之间的比对。从定义到定性依据需要证据支撑,本案证据材料是否能得出“复制”的结论有待商榷。即使构成“复制”,也需要基于各被告人行为的具体特征进行评价,此时,同案犯也可能做出不同认定。比如,前两天写的腾讯内部员工提供程序文件的案例(2015成都CF与逆战外挂案),提供文件的张某与制售团队骨干被定为侵犯著作权罪,负责销售与宣传的汪、吴二人被认定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再比如2019斗鱼人气外挂案中,制作斗鱼、熊猫外挂软件的唐某被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唐某发展的四个下级销售代理被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对于张某、陆某、贾某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三人虽然没有参与外挂制作,但明知赵某制作、销售外挂软件,非法获利,涉嫌犯罪,仍然帮忙测试、解答群内会员疑问等,客观上为赵某留住买家、更好地销售外挂以获得更大的非法利益,提供了帮助,构成赵某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赵某是主犯,三人是从犯。题外话总体来说,如果我们把外挂类刑事判决区分成两个阶段看,可以感知从“2012-2014”到“2017-2021”,法律适用上有一个从“侵犯著作权罪”“非法经营罪”到“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大致变化(不是说类案都定后者,个案肯定还是要看具体的案情和证据,只是后者近年来更为常见)。适用前两个罪名处理外挂类案件,相比私服类,争议较大,在典型案例分析中也会有冲突观点。适用“侵犯著作权罪”处理制售外挂行为时,常见问题至少包括:“复制”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判定“复制”时是否必须进行代码比对?“复制”的对象是什么?“代码”与“数据”是否性质相同?二者的区别是否影响定性?“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保护措施”适用侵犯著作权罪调整还是其他罪名?写这个案子一是个人认为定性有待商榷,二是证人证言令人印象深刻:“……后来我又买了防封号防检测功能,单用外挂会被封号,要和防封一起用,使用外挂后,我的游戏角色比别人厉害很多”。“……我之所以买“海豚”外挂软件,是因为这个软件比较有名气,号称防封。虽然我的号被封了,但客观来说,他们做的防封还是不错。这个客服群有约一千余人,有一个主管和三个副管”。“……这个外挂功能简直太厉害了,我不用外挂,和别人用外挂的对战过几次,我被打得不知东南西北,技术再高也没有用,不知怎么死的,原来有300-400人的战队,现在都没人了”。证人作证时也不忘给好评,看了那么多判决,确实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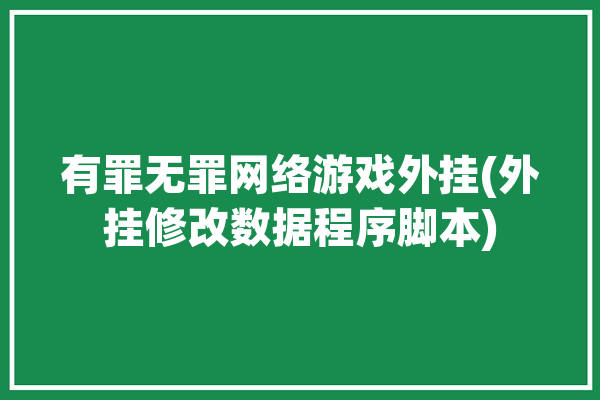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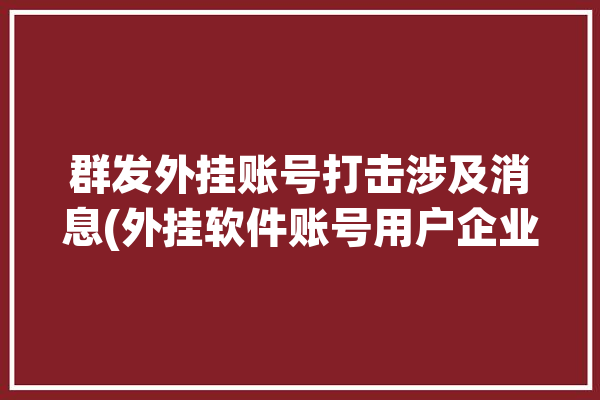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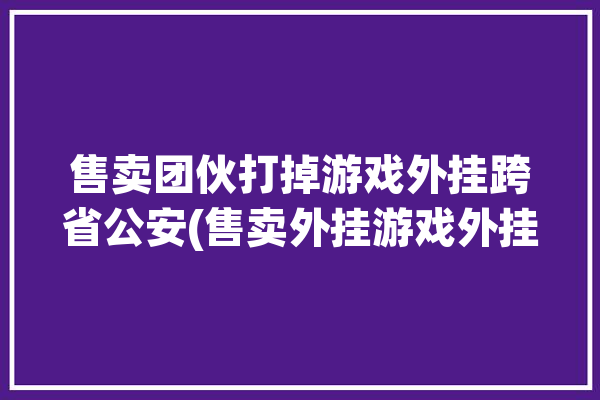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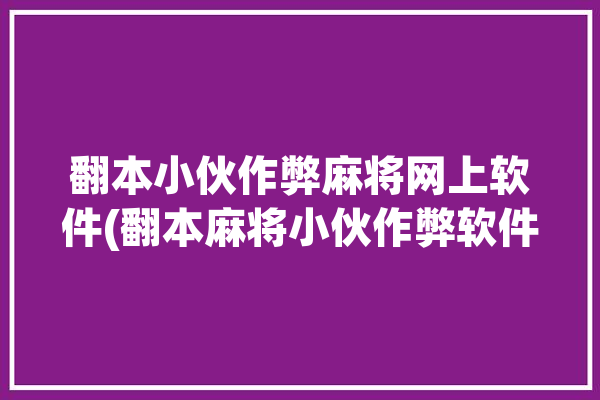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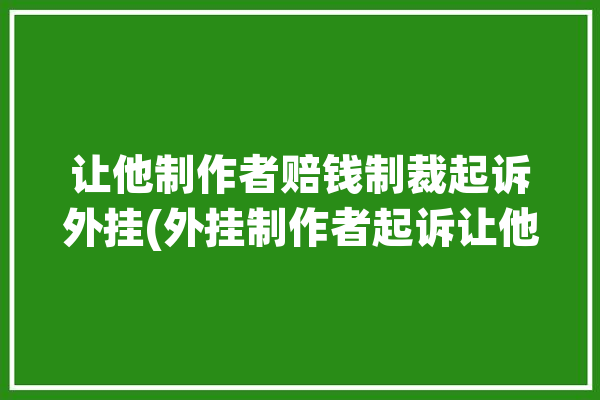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