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难道只注意到他的爪子吗?哦,这样说不对,应该是手。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像猫的人,他前扑的动作、神态,伸开手掌的样子,还有他的灵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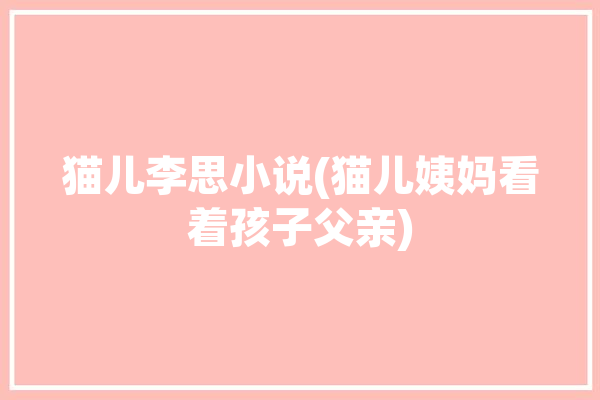
” “他生下来就这样,多动症。
”丈夫见我盯着他,便停下手中的游戏,跟我解释说:“碰到陌生人或者一高兴,就比较厉害。
” “可是......我见过其他有多动症的孩子,人家并不这样。
”我说。 少年叫洋洋,是丈夫姨妈的孩子。 十三年前,姨妈在一家毛纺厂上班。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婆婆,一次偶尔听朋友说有一只猫想送人,便要了过来,交给姨妈养。这事后来让她后悔了一辈子。她压根没想到姨妈会一发不可收拾的开始收养流浪猫,刚开始一两只,后来三四只、四五只。那时候收入低,人多一张口要吃饭,猫多了三四张口一样要许多东西来喂,何况她对猫的宠爱几乎超过她对家里任何人的好。父母自然不允许,她就将猫养在自己闺房里,省下自己那份口粮,与它们同吃同住。 那时候,车间里流行织毛线,别的姑娘下了工就三五个约在一起,织毛线围巾、织毛衣,讨论该织麻花还是菱形方块。唯独她不同。她除了猫,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 但这爱好也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 先是找不到对象。其实姨妈挺漂亮的,瓜子脸,大眼睛,身材也苗条,可是没有人愿意找一个把心思都放在猫身上的女子,你要跟她结婚必须得接受她与猫同吃同睡的癖好。其次是这件事让她父亲和母亲遭受到邻居的众多非议,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天天抱着猫睡觉算怎么回事呢?众口铄金,这话传来传去就越发不堪入耳了。 父母长吁短叹。也曾试着偷偷把她的猫扔掉,但她不吃不喝闹得一家人鸡飞狗跳,父母厌烦了,最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她自己作。 有一次,我的婆婆无意间注意到工厂有一个烧锅炉的光棍汉也养猫,这让婆婆欣喜若狂。后来,这个比姨妈大十岁的光棍汉在锅炉房的单身宿舍与姨妈成了亲。 再后来,有了洋洋。 也不知当时有没有人告诫姨妈怀孕时要对猫狗有所禁忌,也不知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姨妈可曾后悔,因为舍不下寸步不离的猫而致使自己诞下发育不健全的儿子。总之,洋洋生下来不久,他们便发现了他的不同。 洋洋最开始也不叫洋洋,姨妈叫他猫儿。 “猫儿猫儿,你是从我肚子出来的吗?” “看我的猫儿长得多好看。
猫儿,猫儿,你眼睛咋这么好看呢?玻璃球似的。
” “猫儿,你快看,这么多弟弟妹妹陪着你呢。
” 猫儿躺在大床中央,姨妈轻轻揉着他圆滚滚的身子。猫儿被逗得“咯咯”直笑。 她养的四五只猫围过来用鼻子嗅嗅猫儿,用爪子扒拉扒拉他的小手,“喵呜喵呜”的叫。猫儿睁大眼睛,吐着红樱桃似的小舌,“唧唧呜呜”的看着猫们在他身旁打滚。 然而,自打猫儿被查出患有多动症之后,姨妈很快注意到,自己木讷的男人更木讷了,他从来没有真正抬起过的头在这之后便始终埋在了脖子底下。她知道他抵不过旁人的闲言碎语,后来,她只在心里叫他猫儿,在外面,她叫他洋洋。 那会儿,我第一次跟随丈夫回老家探亲。姨妈得知,很高兴地带了洋洋过来。 婆婆家是一套只有六七十平面米的小居室,没有客厅,也没有饭厅,婆婆将自己的卧室隔出一半用来做客厅,吃饭、聊天、看电视。自然,婆婆不会让身上带着异味的洋洋坐进她的卧室,更不允许他擅自进入我们的卧室,她给过道靠墙放个小板凳,那小板凳后来便成了洋洋在这个家的专属座位。 其实,洋洋很乐意坐在那儿,因为坐在那儿没人妨碍他的摇晃和扑抓,没人干扰他的乐趣。 洋洋的乐趣就是开门。在自己家开门,到别人家了也守着门,这或许是他十三年来唯一觉得最得心应手又很快乐的事。每次听到门响,大人还在犹豫,或者象征性的问一声:谁个呀?洋洋发音有障碍,说不了完整的字句,所以洋洋不会问,但凡听到门口有一丁点动静,他就一个箭步跨过去,利落地扭开门锁。不等看清来人,再一个箭步退回来,紧张地望着门口。毫无疑问,他脚步的速度和手指的灵活程度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倘若进来的是他特别熟悉的人,他会兴奋地“噗嗤”笑出声来,然后左右摇摆,手舞足蹈;倘若门开错了,门外并没有人要进来,他便局促不安地埋下头,闪躲着母亲投向他的责备的目光。 洋洋坐在那儿始终无法安静。 只有吃饭的时候例外。洋洋吃饭少有的专心,仿佛因为专心,神经不再能左右他的头脑和上肢让他疯魔。期间,他一次也不会摇摆,更不会将碗端在手上丢出去。无论你替他装多大一碗饭,他都能埋下头,一鼓作气吃个一干二净,而后他会双手捧着碗,伸出细长的卷舌,直到碗光洁如新。 这很不雅观,以至于连姨妈这样与猫整日为伍的人都无法容忍。洋洋被母亲呵斥过无数次,但还是改不了。后来,姨妈也就索性不管了。 姨妈不管了其实是因为心底还存在一丝内疚。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那一天,当她又一次带着洋洋过来跟我们聊天不知怎么聊起管教孩子这事,我的婆婆责怪她不会做母亲,让孩子吃了那么多苦头,现在连孩子的坏毛病都没能改掉。她便可怜地望着过道里的洋洋,很是委屈。 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当年我送走我猫儿是因为我想继续卖菜盒子,你想他还差两个月才八岁,我要是不为卖菜盒子我至于送他去遭罪吗?我背他回来,就跟我屋里的猫一样轻,他都饿得快死了,我不心疼吗?” “可你的菜盒子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停了。
”婆婆好像并没打算在这件事上原谅这个妹妹。 “而且你当时怎么没将屋里那些猫送走?”婆婆再次说到。 姨妈愣了一下,半天没想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图文无关) 当年,她一冲动把猫儿洋洋送到了当地唯一一家儿童福利院。 她也是不得已。那年她失业了,虽然她本来就是个临时工,可临时工好歹每个月还能换回一家人的米面粮油。一旦临时工都做不成了,她便断了买米面粮油的钱,意味着全家的生活只能指望洋洋爸爸了,她于心不忍,锅炉工太苦,她作为妻子至少有责任让他吃的更好一些,何况还有那么多猫要养。她在厂门口摆了个早点摊子,别的不会,炸菜盒子她很拿手。哪知生意只红火了半个月便冷清了,先前说她菜盒子好吃的人买早点的时候都绕着她走。后来,她知道了原因。有人说她不卫生,说她养猫养得把病菌都传给了儿子,说她手上、身上都带着猫的病菌。那天他木讷的丈夫竟然也说:一个傻洋洋丢人还不够,你还要去丢人么?他这样责问他的时候,她看到她的猫儿洋洋不知盯上了什么,正坐在门墩上前俯后仰的“嘎嘎嘎嘎”大笑。她不知怎么突然就冲动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情绪。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她当时厌恶地嘟囔了一句。 猫儿洋洋第二天就被她送进了福利院。 福利院有一大帮像他这样有残障的孩子,比他大的比他小的都有。 在这之前,她去看过,所以她认为洋洋在那里不会孤单。 那天她走了之后,洋洋很安静也很紧张地坐在一间大房子的角落里,看着其他孩子做手工。后来,那些孩子围过来跟他这个新伙伴打招呼,他们热情地叫他“洋洋。
洋洋。
”洋洋那会儿心里一定是兴奋的,他从来没看到过有这么多小伙伴。尽管那会儿他羞怯地低着头,只能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看着他们。但是很糟糕,洋洋他不是那种特别弱智的智障,所以他什么都明白,该死的兴奋会很快让他露出马脚,所以那一刻,他恐惧又沮丧,只能局促不安的拼命揪着手。 但到底也没揪住,他的身子和手像被魔鬼突然拉扯着同时扑了出去,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被魔鬼点燃的火焰,嘴里发出“呜呜呜呜”压抑的声音,谁也搞不清他是在哭还是在笑。 一帮孩子顿时惊恐地四散逃走,远远站定,好奇地望着他。等他能够收回肩膀和手的时候,他像个受伤的刺猬立即紧缩成一团。 洋洋不是眼盲,不是耳聋,也不是小儿麻痹。他所表现出来的肢体上的特别之处令其他残障孩子沾沾自喜,等彻底熟悉了他之后,他们开始取笑和捉弄他。 他们用彩色粉笔在他嘴上画上胡须,在他额头上画上皱纹,哄笑着叫他“大花猫。
大花猫。
”。洋洋似乎也很快习惯了他们的捉弄,他也会随着那帮孩子“嘎嘎嘎嘎”大笑。当他神经不再紧绷的时候,他感到他的肩膀和手不由自主的想舞蹈了,然后他的腿和屁股也离开了凳子。 孩子们的尖叫声和笑声常常惹恼管教老师,等洋洋感觉到身上一阵阵痛楚的时候,他才看到老师高高扬起的木尺。那天,他被罚饿了一整天肚子。后来,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洋洋被罚饿肚子的次数越来越多。 福利院的孩子都会糊纸盒,因为糊纸盒可以给福利院换回足够的粮食和蔬菜。洋洋学不会,不仅学不会,还会因为他的扑抓影响到其他孩子。管教老师把他安顿到角落里一张凳子上,不许他的屁股离开那张凳子。洋洋只能无辜的看着那些孩子,看着那些纸盒越码越高、越码越高,最后像一个个城垛,把孩子的吵闹声、嬉戏声全都围了起来。 洋洋坐着不敢动,他常常把一泡尿憋到中午午饭时再冲进厕所。后来,洋洋发现自己憋不住了。他身上也因此整日带着尿骚味。 日复一日孤零零的静坐让他得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没办法,福利院只奖励那些纸盒糊得多的孩子。两个月后,他的大小便开始失禁,老师便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宿舍。等洋洋妈妈三个月之后接到病危通知的时候,洋洋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像个惨白惨白的面人。 十五岁那个夏天的午后,他一如既往地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向巷口张望。那时候,他已经长成一米七的小伙子了,唇边新生出来的胡须像春天刚钻出土的嫩芽一样鲜亮。以往这样的午后,他也都这样等着他的父亲从巷口走回来,然后拿上肥皂和毛巾带他去厂区的大澡堂子。父亲不和他说话,父亲和他的交流都在眼睛里,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洋洋对沉默的父亲有了许多亲近和依赖。刚开始每次洗澡都是父亲给他搓背,然后父亲再请澡堂的师傅给自己搓。有一次,父亲在他穿上衣服后突然把搓澡巾递给他,指指自己的背,然后把手臂撑在墙面上。洋洋高兴极了,他用羞涩而兴奋的笑告诉父亲,自己手上有使不完的劲。他把父亲的背搓得红透了,父亲一声没吭,接过毛巾时望着他笑了。父亲给他指了指一边洗手的水池子,然后站到淋浴下舒坦地吐了一口气。那天回家,洋洋脸上始终收不住笑容,惹的姨妈猜了老半天。 可是这个午后,洋洋没等到父亲,直到天黑也没见父亲的身影拐进巷子。他跟搂着猫儿看电视的母亲比划,母亲走到门口望了望,又抱着猫退回屋里。等他再次跟母亲比划的时候,母亲吼了他一句:去睡你的觉。
洋洋怔了一下,顺从的爬上了床。他睁着眼睛,然而一汪一汪的热泪很快从眼眶涌出来,这些泪也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他不知道自己明明没有难过怎么会流那么多眼泪。 第二天一大早,工厂几位领导模样的人找了过来。他们看到洋洋的时候,不约而同的皱了皱眉头。 洋洋缩了缩腿,把他们让进屋子。然后,他听见他的母亲突然很大声的嚎哭。那些人很快又一窝蜂似的走了,他的母亲仍然长一声短一声的嚎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靠着墙将身子挪进屋里,怯怯地望着母亲,母亲却一下子扑过来紧紧搂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边说:猫儿,他们说你爸爸脑梗死了,你以后没有爸爸了,你爸爸死了,你晓不晓得?猫儿,你爸爸死了。
你晓不晓得?猫儿…… 姨妈一直想不明白,丈夫的死,儿子怎么会记恨上了她。那天从火葬场回来,洋洋看她的眼神就变了。她想着是时候好好跟这孩子谈谈了。 但这事只在她心里搁了一小会儿便被她忘了。 她有许多事要做,丈夫突然脑梗死了,生活来源就断了,从厂里领了很少一点抚恤金想必也支撑不了多久,她得自己想办法挣钱养活猫儿洋洋,还有那些猫。 这是个古老又颓废的轻工业城市,下岗工人多如牛毛,避过车水马龙、宽敞气派的正街,下岗工人充斥着每条背街小巷两侧的摊点,以及但凡能收容中老年妇女的所有位置。姨妈极度萎靡和沮丧,在这个偌大的城市,她甚至连下岗工人都不是,她只是个依靠丈夫生活在城市夹缝里的贫困居民。城市人不像农村,农村自己好赖有地,退一万步讲只要人勤快,地里种点庄稼随便刨点食就能活命。而城市都是钢筋水泥,要想填饱肚子就得走进各种钢筋水泥的夹缝,抢一个自己的位子。就连摆地摊也有摆地摊的竞争,现在她失去了丈夫这个唯一的依靠,自己又常常丢三落四,甚至连做菜盒子都拿不住面团的软硬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接连一个周,当她游荡完所有能摆摊的地方时,她彻底泄气了。后来,她托了无数次丈夫厂里的领导,他们被她烦得没办法,把她安排到厂区内的大超市做了保洁员。 又一个黄昏来临,猫儿洋洋懒懒地靠在门边的墙上,既不说话,也感觉不到饥饿。他看着天光在高楼之上渐渐暗淡下去,直到完全模糊,而那些窗户上的灯光一点点的亮起来,偶尔一束霓虹从高空闪烁到阴暗的巷道,那灯光耀眼之处仿佛刹那洞穿另一个世界。然而在他拼命想看清什么的时候,光却迅速的隐去,重新坠入阴暗、潮湿和逼仄。 猫儿洋洋的思想也随之坠入一片混沌。他始终没有弄清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似乎明白,他的父亲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 他隐约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自己曾催促过母亲,但母亲只顾抱着猫看电视……想到这,他回过头看看在屋里饿得团团转的四五只猫,母亲还没有回来,出门的时候大概也忘了给猫碗里放些吃食。现在,这几只猫睁圆了眼睛,声音凄厉而急促。洋洋看着他们,看着这些母亲称之为他的弟弟妹妹的猫宠,就像透过一面镜子看到了自己,他感到莫名的愤怒和狂躁。 这情绪使他浑身热血上涌,他的肩膀剧烈晃动,他的手臂快速地左右扑抓,但似乎这样依旧散不开内心炙烤的烈焰。他很快站起身来,连带着麻杆似的两条腿一起晃动,细瘦修长的两条胳膊更像是两只螳螂的前腿——他就这样前俯后仰的冲撞起来,伴随着胸腔发出的“呜呜”怒号,完全进入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癫狂世界。 想必姨妈那天走进巷子心就慌了。 自从丈夫走后,无论她多晚回家她的猫儿洋洋都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倚着墙等她。虽然他一直紧紧地抿着嘴,不再像从前那样兴奋地几步跳过来在她身边绕来绕去,甚至游离的目光偶尔扫过她的脸,她能看出来那里头所隐藏的怨气,但她坚信,她的猫儿是在等她的。只剩下儿子和她相依为命了,儿子无声的惦念于她便是最温暖的慰藉。 可是,这一天晚上,姨妈拐进巷子并没有见到猫儿洋洋。 她敏锐的感觉到就连空气中所散发的气味都跟往常不太一样。巷子幽暗的静谧中,她突然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家里的门开着,她喊:洋洋。
洋洋。
没有人应答。 她一边摸着墙壁上的灯绳,一边继续喊:猫儿。
猫儿。
灯“啪”的亮了,她的视线一下子落到地上,“啊”地一声泪就涌了出来。五只猫摆成花朵的形状瘫软在地上,眼珠可怕地瞪着,嘴里吐出的血变成了乌红,恰好在它们头顶凝结成刺目的圆形花蕊。 这时,姨妈抬头看到了另一双眼睛,那双眼睛茫然而恐惧地看着她。他的身子蜷缩在床角跟筛糠似的抖,而他同样抖着的一双修长的手指沾满了细软的毛和血。 “猫儿。
你个短命的,你都做了些啥。
” 姨妈嚎哭着歇斯底里地扑过去,狠狠地甩了他两耳光。她一把拽住洋洋的胳膊试图把他拖下来,洋洋却用手抓住床沿使劲想挣开她。他们就这样拉扯着,她听见他从喉咙里发出汩汩的声音,像是在吞咽无数的水。就在她伤心地想要松手放弃的刹那,她的猫儿洋洋突然从床上趔趄着扑下将她推到,他把她压在那堆软绵绵的猫身上,用沾满毛血的手指掐住了她的脖子。 姨妈挣扎着。她知道他整日绞手指,手劲一定不小,但此刻,他手上并没有用多大劲摁她。他可怜的看着她,这让姨妈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这个孩子将她扑倒、用手摁住她,就只是为了和她对视一眼。 她后悔极了,她想猫儿洋洋的魂这会儿怕是已经不在他身上了吧,而她刚刚还在打他。她挣扎着喊他:猫儿。
猫儿。
你松手…… 他真的松了手。嘴嗫嚅着,半天,她听到他“呜-呜-”喊叫了一声,随即站起身踉踉跄跄冲了出去。 姨妈赶忙爬起来。就在她追出巷口的刹那,她看到路中间猫儿的身子忽地随一辆疾驰的汽车飞了起来,在那一瞬,她听见他无比清晰地喊了一声:爸——END作者简介 李思纯,现居陕西省石泉县。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百人计划”首批入选作家,《汉江文艺》签约作家,先后出版散文集《泉音倾城》《归处》。嘉年华时光推送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