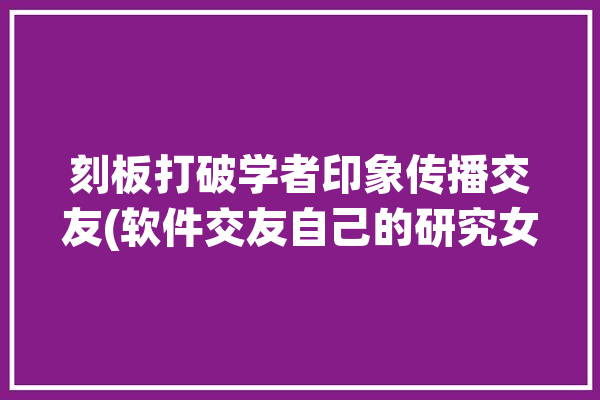
一位传播学学者所做的约会软件研究,为我们理解性别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提起约会软件,或许有许多人会讪笑起来:一直以来,约会软件的“约炮”功能都声名在外,对一些人来讲,使用交友软件,不是一件可以坦率讲出来的事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力深看来,提到约会软件时的讪笑,正是一种社会禁忌的表现。即使到了2021年,社会对交友软件的讨论愈发多样,接受度也越来越高,陈力深依然发现,在自己的课堂上,学生听到交友软件时还是会“笑一笑”。在他看来,这说明交友软件还没有摆脱污名化,而社会放下对交友软件的偏见,不要让“约炮”的标签绑架了大众的认知,才是从约会软件出发,助力性别平权的第一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上,陈力深的个人页面。陈力深从2011年就开始使用约会软件。当时他结束了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硕士学习,回到家乡香港,从事广告行业。后来他决定申请博士继续深造,在构思博士课题时,他发现传播学界对约会软件的研究是个空白。作为一名“没有那么实证主义,注重生活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他很快选择以此为自己的博士课题。2013年,他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最初研究的是男同性恋交友软件。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他决定走出自己也身在其中的同志社群,转而研究异性恋交友软件。他将目光投向了广州,希望了解国内的年轻男女们,如何使用、怎样看待约会软件。2016年和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进行了田野调查,与三十几位约会软件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以此为基础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2018年,他获得南加州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次年,他受聘于本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助理教授。在博士后研究期间,陈力深再次回到广州,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同性交友软件的用户,又采访了三十几位使用者。他将在广州前后共八个月的研究写成了专著The Politics of Dating Apps: Gender, Sexuality, and Emergent Publics in Urban China(《约会软件政治学: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性与新兴公众》),今年3月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陈力深的新书(《约会软件政治学:中国城市里的性别、性与新兴公众》)书封。陈力深说,他想打破社会对交友软件“只是用来约炮”的刻板印象,书中的“政治”,也是讲男性和女性,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这些不同社群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政治运作、选举等。他想探讨的是,在交友、“约炮”之外,对交友软件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探讨的空间?陈力深在研究中发现,直男、直女、男同志和女同志,在使用交友软件时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其背后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关系。他提出,在细微的层面上,交友软件可以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赋权”,例如为女性提供探索自己身体的机会,以及为同志群体带来平权的期待,但在根本上,这些软件无助于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少数权益这些结构性问题。2021年初,水瓶纪元采访了陈力深,以下为访谈节录:交友软件为女性赋权,为同性恋者提供平权想象水瓶纪元:你的研究主要的发现是什么?陈力深:可以分为四类人去讲。我对每一批人问的问题基本都是一样的,从而去留意每一类人在回答时所注重的部分。例如异性恋女性,她们讲了很多交友程序怎么为她们赋权的故事。特别是在广州,虽然是大城市,但大龄单身女士还是会被“剩女”的概念困扰。她们觉得这些软件有机会让她们离开单身行列。这些人也很明白,在交友软件上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欺凌。比如,没有一个受访者在app上没有被男性性骚扰过。女性会跟我讲一些机遇,但同时受到什么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原来单单在手机上下载app,无论你有没有使用,作为一个女性,已经会被人指指点点了。男性完全不会受到这样的污名化。异性恋男性很注重怎样表达自己的男性气质。但中国和外国男人的方法是有分别的。外国的那些通常会放一些运动照、肌肉照,在广州有时我也会看下异性恋男性的的个人介绍,我发现他们很少会放一些肌肉照,反而有三种很明显的图片。第一是扮可爱,尤其是20岁出头那些,有一些韩风,还会轻微美颜。第二个就是喜欢放宠物的照片。第三个是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富。男同志则在约会软件的使用上投射了情感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用具,而是一个符号。例如他们用app的时候,会觉得,今时今日(指2018年调查时)在中国,我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地结交同性伴侣。这对他们有很大鼓舞,让他们觉得,将来中国在同性平权上都会有进步。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后话了,比如上海骄傲节被取消。2018年的时候,性别平权相关的活动还没有现在这样死寂。与之对比的是,美国男同志用交友软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性别平权的象征,就只是觉得这很方便,可以约炮、找男朋友。至于女同志,有趣的一点是,她们软件的设计是不同的。像LESDO、热拉这些,她们很注重社区的模式。一打开软件,首先见到的就是社区的帖子,而男同志或者异性恋那些,一打开就是一格格不同的人。我有一个访谈对象,本身是社工,她在上面免费帮人做心理咨询,在我所有的受访者里是独一无二的。她很肯为这个社群付出。2018年上海骄傲节。图片:法新社水瓶纪元:为什么女同性恋的交友软件会更注重社群建构?陈力深:关于这个我没有做二次研究。但已经有研究者采访了热拉的创办人,得知创办人本身对社群的想象很强烈。这个创办人在采访中不断讲,自己身边有很多女同性恋的朋友,这些女同志很优秀,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又觉得男同志会更注重性,而女同志更喜欢聊天。所以他在做热拉时就希望设计一个软件让大家可以多聊天,就更注重做成社区的形式。如果从批判的角度看,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对女同志有这样的想象呢?为什么觉得女同志不倾向约炮呢?他是怎么得来这样的想法呢?是他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得到的,还是他被“女性在性上是保守的”这一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和这种对男女的双重标准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是有的。设计者会带自己的概念进入产品。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剃须刀。很早以前男女是一起用的,没有分别。直到有一天,设计者觉得,男人对科技更有兴趣,就可以设计专门针对男性的剃须刀。所以现在男性的剃须刀设计是很“透明”的,刀片一般是裸露的,你可以很轻易看到内部结构,也可以很轻易拆下来清洗。女性的刮毛刀,现在的设计是很流线型的。男性的剃须刀是清洁用品,女性的刮毛刀变成了护肤用品。所以设计者会不自然地把自己的偏见带入产品里面,无法抽离出自己在社会建构中已经吸收的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不过,不同的约会软件,他们在功能上都是相似的,是要让你认识陌生人。软件的设计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用户,而是出现的时机会有影响。年轻人可能会在新软件出现之后转移去新软件。越早出现的软件,用户可能会越复杂,而不是软件设计有根本的区别。比如,我在2018年听许多男同志受访者说,Aloha上面的人素质比较高,好过Blued,比如用户更年轻,而Blued会有一些40、50岁较年长的男同志使用。另外就是Aloha上面的人“颜值”更高。2016年我在和异性恋受访者聊天时知道的情况是,陌陌刚出现不久就被人批评是约炮软件,所以当时他们觉得探探好过陌陌。后来一两年,我和这些受访者保持联系,他们开始觉得探探也变得越来越偏向约炮了。2016年到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陌陌和探探是异性恋访谈对象最常使用的交友软件。图片:视觉中国水瓶纪元:网上有一种讲法,所有的社交软件,不管是不是约会软件,其最终目的都是“约炮”。陈力深: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不如说所有的沟通最终目的都是性。要约炮的人不需要用交友软件,用什么都可以。交友软件和约炮画上等号,一个原因是外界的报道更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在我的研究里,包括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很多人在这些交友软件上并不见面,纯粹聊天。我在研究陌陌的时候,有几个访谈对象本身在广西生活,去了广州打工,陌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友平台。他们不能在微信上吐槽,不想被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广州这么辛苦,唯有在陌陌上讲。因为陌陌是按照地区划分的,他们可以在陌陌上讲很多广州生活的艰辛,并获得共鸣。所以说,“约炮软件”可以不是用来约炮,要看用户在这个环境里想得到一些什么。水瓶纪元:关于对交友软件多样化的使用情境,你在访谈过程中还遇到过哪些比较有趣的故事?陈力深: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直女——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偏见,因为和男性做访问可能半小时就做完了,他们讲一两句就完了,而女生会讲很多故事。有一个是来广州读硕士的,她说她从小在性教育上是缺失的,不懂什么叫恋爱,什么叫性。在广州,她想学好英文,将来去国外读博士。她在探探上主要和外国男人聊天,认识了一个欧洲男人。这个人和她说,你对这个世界完全都不认识。她听到之后觉得自己很像一只井底蛙,于是开始看很多外国新闻。这个交友软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她对世界的好奇心。还有一位受访者,我每次回广州的时候都会和她见面聊天。2018年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可能是双性恋。我就想,2016年的时候你还是直的呢,因为我回美国之后她还跟说,美国的男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会不会更绅士?不如介绍些美国男人给我?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她很直。那天她在吃雪糕的时候跟我说她是双,我很惊讶。我就跟她介绍说,如果你想试下认识女同志,可以用女同的交友软件。2020年初的时候,我写书到了结论的部分,我就想问她的近况。她说还是觉得自己是直的。我就觉得,如果没有交友程序,她也不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双性恋,原来交友程序可以让人探索自己的性取向。我整天讲,交友软件不只是约炮,这两个案例就很典型。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探索,是超越约炮的。广州街头。图片:视觉中国在约会软件上,直男依然处于权力关系的优胜地位水瓶纪元:这其中会否有一些隐藏的权力关系?比如不同性别、性取向的人,在约会软件上其实并不对等。陈力深:如果去对比直男和直女的话,交友软件的确让女性在性上寻找新的挑战,或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女性始终避不开刻板印象。用交友软件的时候人们说你是荡妇,不用的时候人们说你是剩女。在个体的层面上,交友软件确实有为女性赋权的作用,但放在整个社会上,作用微不足道。交友程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为科技无法解决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对男女的刻板印象,以及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我在采访直男的时候,他们会说,在探探、陌陌上,很多女人是“妓女”、酒托和销售。他们就说,这些女士不应该用交友程序做这些“商业行为”。我的看法是,广州有很多打工人,男女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轻易找到工作,女人未必,她们在人力市场上已经比男人的机会低了一截,所以一些人为了生计可能去做性工作,或者要去做酒托,然后男人再说这些人不道德。我在书里是很批判这件事的,我说男人去批评这些女性,是第二次利用自己的性别红利。第一个红利就是在人力市场上,第二个是在约会软件上。之前讲过,同志交友软件给了同志们社群的资源,带给他们远景和期盼。但如果我们检视这些软件,还是会发现问题。比如女同的软件是要求讲自己的性别身份的,像T、P、H,这些不就是将女同志的关系嵌入异性恋的想象中吗?一段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更女性化的角色和一个更男性化的角色吗?而热拉有拍一个网剧,叫《热拉帮》。这是一个时尚的故事,背景在上海。问题是,里面的女同志有两个很男性化的角色,去争取一个女性化角色的欢心。这也是将同性关系放入异性恋的模式中。我想在书里呈现出这种张力。交友软件在带给用户期待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压力。水瓶纪元:你刚刚提到约会软件对女性的赋权,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陈力深:赋权(empowerment)这个词本身在不同的学科上有不同定义。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是女性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经济上获取更多机会、更多资源。而我们在这里讲的赋权,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一个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大胆去选择一个男人?一个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去约炮呢?一个女性是否可以在使用交友软件时了解更多自己对恋爱的看法?或者是否可以将爱情和性分开?我们华人社会本身性教育就不够,很多家庭没有很多机会给女生空间去进行这样的反思。交友程序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这不是经济上的赋权,但在理解自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但交友程序本质是一种科技产品。我前面所讲的男女,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科技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政府政策、教育改善、媒介素养的训练来解决,科技只是其中一种元素。我在书中强调了一点,交友软件确实可以让女性和同志群体去发现自己,但我们要记得,中国社会现在的社会脉络,对女性依然不够保护,对同志权益依然不够重视,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水瓶纪元:交友软件对用户还有没有其他潜在的危机?陈力深:所有人都有。但不同群体遇到的最大困扰是不同的。直女和男同志是很相似的,就是被性骚扰。这两个群体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告诉我他们被性骚扰过。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交友软件上性骚扰的成本太低了,发一张照片给你,你也不知道是谁。虽然你可以投诉,但对方再开一个新的账户就行了。直男本身在性别权力关系上是优胜一方,不会担心被性骚扰。他们遇到最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被人骗。他们觉得很麻烦,要在聊天时慢慢去猜对方是什么人。所以有男人跟我说自己已经有经验,先看这个女生的账户是什么时候开的,如果少于三个月,他就会感到危机。女同志最大的忧虑就是,她们会在这些社群的讨论里见到很多勾心斗角。一个受访者说看过一个直播,里面的人就公开谁偷走了我的女朋友。本身软件设计是希望建立社群的,所有会有很多直播和讨论区,这些途径同一时间也可以做一些破坏社群的动作。每一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也是因为在社会建构上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我会决定分开去写。我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审评人觉得,我这样划分,是不是在制造性别和性取向的二元对立呢?我自己在书里说,我是一个酷儿理论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是不是矛盾的?我承认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现实中的确还有这种分野,并导致了约会软件上不同的使用经验。我不可以抹杀这些生活上的分别。我觉得这样将每个群体抽出来讲他们的机遇和挑战,好处是多于限制的。“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没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水瓶纪元:你做交友软件研究的这些年,社会大众以及传播学界对交友软件的关注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力深:我觉得是大家讲得更多了。现在媒体也会讲交友软件的多样化,很多用户不会羞于承认自己使用交友软件。但有时学生讲交友程序时,还是会笑一笑。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讲一些“禁忌”。当大家还在对这件事笑一笑的时候,这仍然不是一件被主流社会正视的事情。相比我2013年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学界现在多了很多论文。每个月我都会至少收到两篇需要评议的论文。交友程序一开始的研究,尤其是同志交友,最开始都是用公共卫生角度看的,是讲HIV和性病的预防以及安全套使用。中期才开始讲人际关系沟通,比如人们在上面怎么展现自己的不同,在上面聊天的范式有什么不同。后期就开始讲交友软件背后的政治,在社会上的意义,对权力关系的彰显,比如平权、赋权、性少数的社群营造、怎么对抗异性恋霸权。今天我大部分看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些内容。短期来看,我想不到会有什么新的突破,除非你去一个和欧美、中国都很不同的地方。最近我看过一篇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的文章,讲菲律宾女性怎么用交友程序。很特别的是,它讲到Tinder对菲律宾女性来说是直接走向国际的桥梁,因为她们觉得可以直接跳过菲律宾男性,直接认识白人,这其中有一些对白人的迷恋。从我个人来说,2019年我回到香港,要备课,准备新生活,没有什么时间。2020年才重新开始做研究,上半年在香港做了一个交友软件与政治立场相关的研究。我不断在想的问题是,在交友之外,交友程序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我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现象可以在小事上反映出来。香港街头。图片:法新社水瓶纪元:我自己的观察是,在内地,也会有很多人在个人介绍上写明自己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比如对性别议题的看法,对一些特定社会事件的看法。几年前在你做研究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吗?陈力深:有的。而且其实美国也有这种情况。现在美国很多人会在Tinder上写BlackLivesMatter(黑命攸关)。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潮流。这其实是件好事。我觉得即使你不同意,但你写了出来,一些本身同意但不够胆讲的人,会因为你写了出来,就敢讲了。整体来讲是有部分作用的。我最近常讲,BlackLivesMatter变成了一个New Sexy。在内地,可能用户会事先写明对性别平权议题的看法,也可能是很小的事,比如“我一定不会做家庭主妇”。这些是很进步的。但回到之前的问题,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的问题,科技只是拼图的一块。一个社会整体的改善,要靠政府政策、教育和媒介,缺一不可。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没办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水瓶纪元:你当时在广州做了田野调查,访谈对象是怎么找到的?陈力深:我在做广州这个研究之前,在美国也是做交友软件研究的。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找男女同志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决定先找直女的访谈对象,这个群体我可能最不熟悉。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她刚好2016年的时候在广州有个公开讲座,讲女性性自主。我就问她可否在这个讲座上宣传我的研究,她说可以。之后我自己也有下载陌陌和探探。这些都是要大学的伦理委员会去批准的,也就是说用这些软件的目的只是做研究,不能让其他人误会我是在上面做其他事情。我先是通过这两个方法找直女访谈者,之后她们也有帮我找她们的朋友。当时交友程序不是很普遍,很难在软件之外的地方找到受访对象。而现在可能在网上问一下,就会有很多人回应。直男我就不能在交友程序上找,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男的。所以这些访谈对象主要是之前那些直女帮我介绍的。男同志和女同志我是通过广州的两个同志团体找的。我自己其实也很介意用交友程序找受访者。我自己是同志,如果我在男同志的社交软件上出现,虽然我是一个学者,说我在做研究,但很容易被人误会我有一些其他的企图。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是说,包括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你要想一想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别地位、种族的身份,在某个场所找受访者,这件事是否有危险?不是说身体上受伤害的危险,而是会不会有一些你没想过的意外出现,而导致事后人们会质疑你研究的公信力?所以直女我可以自己用交友软件找,因为可以直接说,各位,我对你们没兴趣。其他人就很难这样找。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使用探探寻找访谈对象时所使用的个人介绍。图片:受访者提供水瓶纪元:这其实也是做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时,研究者需要反思的positionality(位置性)的问题。你在做这项研究时,怎么看待自己的特质、地位会给研究带来的影响?陈力深:我会想,对女性的访问,我是一个男人。对男性的访问,我是一个同伴。其中对男同志的访问,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只是想访问,而是想有后续的。而对女同志的访问,她会觉得我是平权上的伙伴,对我在私人生活上完全不会有想象。这些我在做研究时是很注意的。我会想为什么男人会和我说这些呢?其中有两个人跟我说,他们很喜欢骗女人,英文叫Pick-up Artist,也就是PUA。他们一个礼拜约三四个人出来,发生完关系就不理她们了。他们会自吹自擂地和我分享,觉得这是一项技能。如果我是一个女人,他们不会跟我说这些的。访谈的时候,我不能在听到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立马生气,只能继续听,希望他们继续讲下去。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我好像鼓励了他们做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反对,我只是很沉默地坐在他面前。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就是自己在访谈时,为了让对方讲自己平时不会和其他人讲的事情,会不会同时鼓励了他们去做和我本身立场相违背的事?而女性那边,如果在合适的情境下,我会向直女透露我的性取向,让她知道,这个访谈是纯粹学术的,而不是希望通过访问有一些其他的期待。因为有人在陌陌上回复我,哇你用这个方法约炮,很新奇呀。我自己也要留意,我用男性的身份去访问女性,不是问她们对经济、对时装的看法,而是关于性、爱情、交友程序的看法。这在一个男女对话的环境下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会尽力让自己更专业,比如我会带之前发表的文章,访谈前给对方看。我也会选择一些既开放又可以有两个人对话空间的咖啡厅进行访谈。水瓶纪元:会不会担心这样找受访者会有一些bias(偏见)?比如你在性自主讲座上找到的人,可能都会偏向类似的价值观,她们找到的朋友,可能也都是相似的。陈力深:做质性研究,比如为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一个受访者肯接受一个小时的访谈,一定是有一些性格的。一些不喜欢讲话,想避开这些话题的,本身也不会参与这种学术研究。所以做访问,我想我们要理解,这个方法本身是有限制的,因为有些人我们是找不到的。我知道会有bias,比如她们更喜欢表达,如果是同志的话会对平权的关注更强。我要接受这些研究的限制。但我的研究也正正是想知道,一批用交友程序的人,交友程序怎样影响他们的权益?如果这些人本身对权益很有概念,他们正适合做我的访谈对象。所以这个bias是相对正面的。水瓶纪元:你觉得在2021年,大家对约会软件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陈力深:我觉得要乐观而谨慎。我不能讲交友程序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上面会有性骚扰,可能会有隐私的泄露。我想说的乐观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交友软件只是约炮的,我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会怀疑学术研究和大众的沟通依然有距离。即使我们发现用户的心态很多,有想约炮的,有想找长期伴侣的,也有些是纯粹在等地铁时看下帅哥美女的。但这些结果还没有和大众产生太多交流。而且更深层面上,我们之前聊到背后的性别议题,又有多少大众会知道我们研究者为什么要做这些呢?——————请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全现在”,朋友圈的世界也会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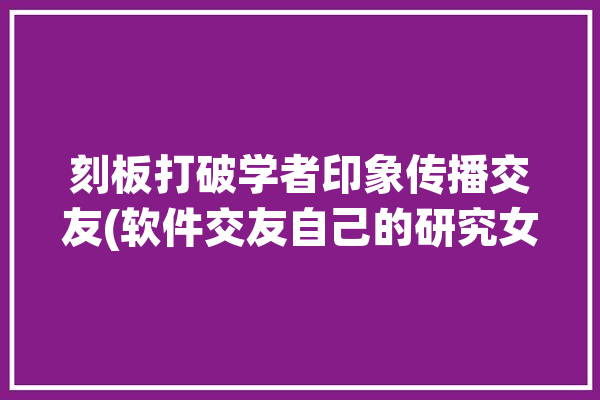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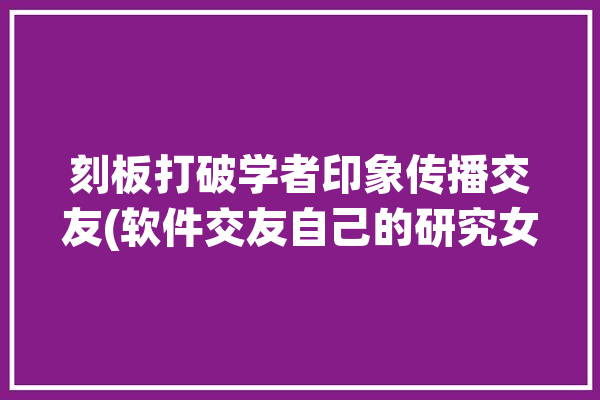
0 评论